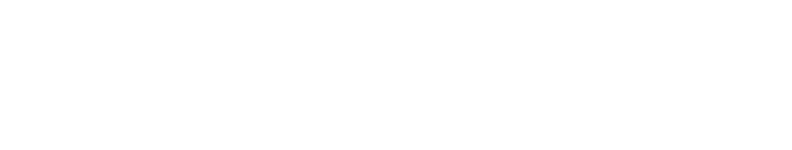为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读书月期间,集团开展了“一本书·一个世界”主题征文活动。集团干部员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文致心,以笔抒情。有的在阅读中探寻红色基因,有的记录下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有的抒发与时代同频的青春梦想,有的以故事表达对生活的期许与热爱。现将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分享,开启一场充满书香的旅程。
一江春水映初心
——读《赣江怒涛》
集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熊政纲
清明时节,杨柳吐绿,细雨如烟,我驱车沿着赣江两岸返回故乡丰城,迎着扑面而来的泥土与书页混合的清香,踏入了镇上老旧的小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角落里,翻开一本积尘泛黄的《赣江怒涛》,1940年代丰城、樟树一带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红色记忆,如一幅血与火绘就的画卷徐徐展开,书中详细记载了游击队利用赣江流域复杂的水系地形与日寇展开的激烈斗争,与北方平原游击战形成鲜明对比,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聚焦井冈山、瑞金而忽视赣中战场的缺憾,充分展现了江西革命斗争的多样性。

这是闪耀在渔火里的革命星芒
书中最令我动容的,是关于渔船的细节:“船底垫着棉被,连摇橹声都隐没在江涛里。”这哪里是简单的战术描写?分明是一幅浓缩的革命画卷。我仿佛看见春寒料峭的夜晚,赣江上雾气氤氲,二十余名游击队员蜷缩在三条小渔船中。那些棉被,或许是从新婚妻子的嫁妆里拆来的,或许是老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此刻却成了革命的屏障。船头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火,在漆黑的江面上划出一道微弱却倔强的光痕,照亮的不只是前行的航道,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的希望。
“班长把最后半块糍粑留给发烧的战士,自己偷偷吃观音土。”这行简短的文字,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在市博物馆里,我曾见过那种灰白色的观音土,像极了冬日里未化的残雪。想象那位不知名的班长,是如何在战友熟睡后,就着冷水咽下这哽喉的泥土。他的胃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他的心却比赣江最清澈的江水还要明净,这半块糍粑的分量,重过千钧。
渔家女阿莲的故事最是锥心刺骨,这个本该在晨光中唱着采菱歌的姑娘,却在敌人的刑场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她嘴角挂着血丝,却对我们露出微笑。”这微笑里,没有恐惧,没有悔恨,只有江风般的纯净和山花般的烂漫,让我想起在赣南采风时见过的野蔷薇,越是风雨摧折,开得越是绚烂。
这是垂落在怒涛中的时代倒影
赣江在书中不仅是战场,更是一个有灵性的存在。春季的怒涛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夏日的湍流似万千银箭齐发。这条贯穿江西南北的水系,时而温柔如母亲的臂弯,时而暴烈如复仇的利剑。它见证过最黑暗的背叛,也孕育过最纯粹的革命,“江水记得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
游击队发明的“芦苇荡电台”令人拍案叫绝,他们把缴获的电台藏在芦苇深处,用竹管做天线,以鹅群叫声为联络信号。清晨的薄雾中,放鹅的老汉哼着小调,谁能想到这悠扬的曲调里,藏着关乎生死的密电?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斗争智慧,与北方地道战、地雷战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中国人民的战争智慧史诗。
“学生兵”小周带着《红楼梦》参加革命的情节尤为动人。在战火纷飞的间隙,他总爱倚着老樟树读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炮声如雷,我却梦见大观园里的海棠开了。”这种文化传承与革命精神的交融,恰似赣江与鄱阳湖的水乳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这是振荡在涛声里的当代回响
如今站在南昌港的观景台上远眺,但见千帆竞发,货轮如梭,八十年前游击队的小渔船,已化作万吨巨轮;昔日的“水上交通线”,正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江风依旧,涛声如昨,只是那浪花里跃动的,不再是硝烟,而是朝阳般的希望。
当书中战士嚼着松针坚持战斗的画面,与当代青年抱怨“996”的朋友圈并置时,这种时空对话发人深省。在丰城市石滩镇的烈士陵园里,我看到一群红领巾正在扫墓,有个小女孩指着纪念碑问:“老师,他们为什么愿意吃树皮?”这个问题,或许比任何教科书都更能触动人心。
令人忧心的是,书中记载的17处战斗遗址大多已无迹可寻,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那些浸透鲜血的土地,正在变成物流园区、商业综合体。记忆的消逝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所幸,还有一些人在行动:地方志办公室的老张,花了十年时间走访幸存者;小学教师李梅,带着学生们排演红色话剧《赣江怒涛》……
每个人都是大江大河里的一朵浪花,既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又折射着时代的光芒。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虽不用在枪林弹雨中撑船,但要在改革深水区中“撑篙”,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就是对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赣江永远向着大海奔流,一个民族的灵魂,永远向着光明生长,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浪花,终将在我们的记忆中,化作永恒的星辰。